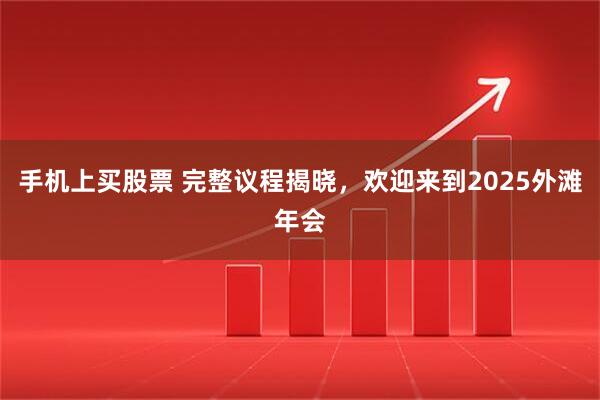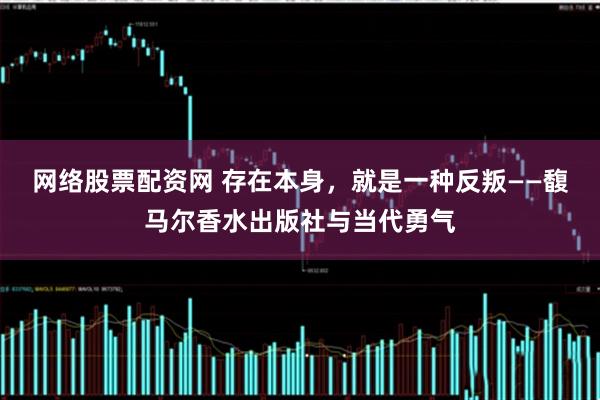
在馥马尔香水出版社,香水从来不是标价商品,而是“可被品读的作品”。
有一个奇怪的现象: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在展示自我的时代,却越来越少有人敢于真正“被看见”。
展开剩余93%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精心策划的“人设”——每一张照片都经过滤镜修饰,每一段文字都符合人设定位,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。我们不是在展示自己,而是在展示“别人期待看到的自己”。这是一种安全的表演:只要按照剧本来,就不会被质疑,不会被拒绝,不会暴露出那些我们自己都不太确定的部分。
《亚威农少女》
巴勃罗·毕加索,1907年
Portrait of a Lady肖像灵感:毕加索立体主义
真正的肖像却恰恰相反。它不是镜子——镜子只会忠实地复制你此刻的表情。肖像是一种更残酷也更诚实的东西:它试图捕捉你的全部,包括那些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侧面。毕加索画《亚维农的少女》时,将女性的正面与侧面同时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,这种“不合理”的处理恰恰道出了一个真相——人从来不是单一的、扁平的存在,我们总是同时拥有多个面向,有些甚至相互矛盾。
品牌挚友Konstantin Kakanias为Portrait of a Lady创作的插画
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肖像令人不安。它拒绝让你躲在某个安全的标签后面,拒绝让你只展示“好看的那一面”。它坚持要呈现完整的你:温柔的与强硬的,优雅的与粗粝的,被看见的与被隐藏的。
视觉可以欺骗,文字可以修饰,但气味有一种奇特的诚实性。
当你走进一个陌生的房间,还没来得及观察细节,气味就已经告诉你一切:这里住着什么样的人,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,甚至他们此刻的情绪状态。气味绕过了大脑的理性审查机制,直接抵达记忆和情感的深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易忘记一个人的长相,却永远记得他身上的气味。
Portrait of a Lady肖像调香师Dominique Ropion
调香师Dominique Ropion在馥马尔香水出版社——这个世界上唯一以“出版社”模式运作的香水品牌——创作Portrait of a Lady(“肖像”)时,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他拒绝创作一款“讨人喜欢”的香水。传统香水工业的逻辑是清晰的——前调要足够吸引人,好让顾客在柜台前停留;中调要安全舒适,不能冒犯任何人;基调要持久但不张扬,成为一种“得体的背景音”。这种设计哲学的本质,是将人简化为消费者,将复杂的个体简化为某个市场细分里的统计数字。
但Dominique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他让大马士革玫瑰与广藿香、檀香的沉稳木质调发生碰撞。这种组合在传统香水语法里几乎是“不合理”的——就像毕加索把正面和侧面画在同一张脸上一样“不合理”。玫瑰在这里不再是“女性化”的象征,而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力量宣言,一种几乎具有侵略性的存在感。
恰恰是这种“不合理”,让“肖像”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肖像,而不是一张美化的证件照。
“某些分子远比其他更有力量,轻如羽毛亦能撼动大象。”当Dominique说出这句话时,他谈论的不仅是调香技艺,更是一种对待创作的哲学态度。
在钟表匠的工作台上,一个细如发丝的游丝决定了整块表的精准度。在建筑师的图纸上,一根看似纤细的钢索承载着整座桥梁的重量。艺术创作中最迷人的时刻,往往发生在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平衡被实现的瞬间——当轻盈撼动沉重,当柔软驾驭刚硬,当一个微小的决定改变整个结构的命运。
Richard Avedon的经典之作《Dovima With elephants》
Dominique在创作“肖像”时,进行了数百次配方调整。这不是简单的试错,而是一场关于临界点的探索:他要找到那个精确的刻度,让高浓度的玫瑰既不被广藿香的沉稳淹没,也不让木质基调显得笨重。每一个分子的剂量都经过严密计算,每一次微调都可能打破整个平衡。这种工作方式,与其说是调香,不如说更像雕塑——米开朗基罗面对大理石时的那种状态,相信完美的形态已经存在于石头内部,而他只是将多余的部分凿去。
这种近乎偏执的钻研精神,恰恰是馥马尔香水出版社所坚守的核心价值。在一个追求效率、讲究“快速迭代”的商业时代,馥马尔给予调香师的是最奢侈的东西:时间的自由、失败的权利、推翻重来的可能。没有截止日期的压迫,没有成本控制的束缚,没有市场数据的干扰。调香师可以像梵高对待向日葵、像莫奈对待睡莲那样,反复试验,直到抵达那个只有自己才能看见的“完美”。
这不是浪漫主义的姿态,而是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:真正伟大的作品,从来不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任务,而是在漫长的探索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生命体。羽毛撬动大象——这个绝妙的平衡不是被“设计”出来的,而是被“发现”的。它需要的不是聪明,而是耐心;不是技巧,而是信念。
1890年,梵高在奥维尔的麦田里开枪自杀,此前他一生只卖出过一幅画。1874年,莫奈的《印象·日出》在首次展出时被评论家嘲笑为“壁纸草稿都比这完整”。1913年,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在巴黎首演,观众在剧场里打成一团,认为这是对音乐的侮辱。
这些故事今天听起来像是笑话,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真正超越时代的艺术,往往在诞生之初不被当下接纳。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好,而恰恰因为它们太超前——它们挑战了既有的审美习惯,打破了安全的创作边界,提出了尚未被理解的美学命题。
馥马尔香水出版社创始人Frédéric Malle
这就是馥马尔所说的“明日经典”的真正含义。它不是一句营销口号,而是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信念:相信那些今天可能不被理解、不被看好的作品,恰恰可能是未来最珍贵的遗产。这种信念在商业逻辑上几乎是自杀式的——在一个要求即时反馈、快速变现的时代,把赌注押在“未来”上意味着放弃当下的掌声和利润。
但如果回望历史,那些真正留存下来、被一代代人珍视的作品,哪一件不是曾经的“异类”?印象派绘画最初被官方沙龙拒之门外,现代主义建筑曾被视为对传统的背叛,爵士乐刚诞生时被认为是“不成调的噪音”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:拒绝迎合当下的流行趣味,坚持表达那些尚未被命名、尚未被接受的真实。
馥马尔的“明日经典”哲学,是对这种艺术规律的深刻理解。他们给予调香师完全的创作自由——不做市场调研,不设时间期限,不限制原材料成本——这种模式在商业上看似“不理性”,实则是在保护艺术创作最核心的东西:让创作者有勇气去创作那些“当下不一定被接受”的作品,让他们有空间去探索那些“未来才会显现价值”的方向。
这是一场关于时间的豪赌。赌的不是运气,而是对艺术价值的终极信任:相信真正触及人性深处的作品,终将超越时代的局限,找到它的知音。就像梵高的向日葵最终悬挂在世界各大博物馆,就像《春之祭》如今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作品——时间会证明,那些最初的“误判”恰恰指向了真正的经典。
向左更多
当馥马尔在调香师的瓶身上并列署上创作者的名字,这不是营销噱头,而是一种宣言:香水不是匿名的工业产品,而是有灵魂的艺术作品。它等待的不是今天的销量,而是明天的共鸣——当多年以后,有人在某个瞬间闻到这个气味,突然理解了创作者当年想要表达的一切。
我们习惯了用性别来分类世界:男香、女香、中性香。这种分类看似理所当然,实际上暴露了我们想象力的贫乏。
为什么玫瑰就一定是“女性化”的?为什么木质调就一定是“男性化”的?这些关联不是自然法则,而是文化建构——是广告、是市场营销、是几十年来被反复强化的刻板印象。它们的作用是简化选择、降低认知成本,但代价是剥夺了我们体验复杂性的能力。
“肖像”最激进的地方,在于它拒绝这套语法。它的骨架是典型的男香结构,核心却是大剂量的玫瑰。这不是“中性”(中性往往意味着回避、妥协),而是同时拥抱了两种看似对立的特质。就像那些最有魅力的人,往往同时拥有刚与柔、强与弱、进攻性与脆弱感。
Helmut Newton的肖像照,
Alice Springs于1987年,摄于蒙特卡洛
这让我想起赫尔穆特·牛顿的摄影。他镜头下的女性既是强悍的又是脆弱的,既是欲望的主体又是被凝视的客体。这种复杂性不能被简化为“女性主义”或“物化女性”——它拒绝被任何单一的政治标签收编,因为它呈现的是人的真实状态:充满矛盾、无法被简化。
当你喷上“肖像”,你不是在选择“男香”或“女香”,你是在宣称:我拒绝被这种二元对立定义。
馥马尔一直用黑色瓶身——黑色代表思索、内敛、深度。但这次,红色蔓延了。
馥马尔门店艺术展现场
红色是一种危险的颜色。它太直接、太情绪化、太“暴露”。在一个推崇“高级感=性冷淡风”的时代,红色显得既激进又不合时宜。但也正因如此,红色是一种姿态——它拒绝躲藏,拒绝含蓄,拒绝“低调”。
法国视觉艺术家Adeline Mai为PORTRAIT(S) OF A LADY “肖像”
创作的拼贴作品
红瓶“肖像”的主题是“expose”——暴露、展示。这个词在当代语境里充满张力:它既有揭露真相的勇气,也有不顾一切展示自我的决绝。在一个人人都在小心翼翼管理“人设”的时代,这种彻底的暴露几乎是一种反抗。
它在说:看见我,完整的我,不加修饰的我。
你不是在“使用”一件商品,你是在展示一幅肖像——关于你的肖像。
这幅肖像包含了你的正面:那个直视世界的炽热目光,毫不掩饰的存在感。它包含了你的侧面:转头瞬间的优雅轮廓,那些不经意流露的从容。它也包含了你的背影:转身离去时的深邃剪影,那些不需要解释的余韵。
发布于:北京市华生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